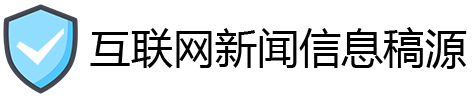文/圖 高翔
風雪是風景。
那風,像卷曲的發,從左院墻上翻過來,然后裹挾著廚房煙囪的藍煙,卷曲著拐進右院的空巷里。那風,像無形的手,一陣陣地按壓著溪邊那棵柳樹,柳樹忽而向左邊彎,彎,一些枝條就碰到了地面。柳樹忽而又向右邊彎,彎,枝條在水里不停地狂草著漢字。順著風,刀片一樣的雪,于是就橫著飛,扭著飛,旋著飛······在卷風飛雪里遠眺,天地是一片蒼茫,一眼望不到邊。
夜里,聽到屋后“咔嚓”一聲破裂的脆響,然后是撲地一聲悶響,像是有人重重地摔在了雪地里。想屋后有一片竹,一定是某根楠竹壓破了腰桿,記得2008年那年,也是這樣的聲音,晨里去看,楠竹被雪壓破折了好幾根,白白的竹骨森然驚目,裂口邊緣鋒利得驚心。原本是竹的苦難,卻又殃及了魚池。在楠竹邊的那一棵紅梅,開得正艷極,卻被竹梢硬生生地壓斷了一半枝丫,斷枝歪歪斜斜地插在雪地,梅花瓣跌在雪地,如血滴觸目驚心。幾根楠竹的青春,也就夭折了;一棵梅樹來年的轟轟烈烈的事業,也就黯然失色了。一棵植物,要活過風吹雪壓的冬天,磨難總是少不了的。但讓人慶幸的是,那棵梅樹殘著身子還活著,每年風雪里,依然堅韌不屈地開花。
晨里,雪小了,但還在下。屋檐下的衣篙子上,歇著一群麻雀,褐色的羽毛被風吹得忽立忽伏忽扭忽聚,紛亂不堪。它們正歪頭歪腦地一會兒看看茫茫飄雪的天空,一會兒看看空寂的原野——連一顆玉米都找不到了,本來就餓肚子,卻又遇到風雪天氣,如何是好?它們內心凄苦著。忽然麻雀們異常地叫嚷起來,原來發現離它們不遠處,散落著些許稻谷。當然,它們憑經驗也知道,在谷粒旁邊的某一隱蔽處,應該有孩童的彈弓正瞄準著它們。去年的風雪天里,就有一個同伴被彈弓打中了腦袋,一陣抽搐痙攣后,永遠離開了它們。這卑微的生靈,在這風雪天里,僅僅只是為了一口飽肚的吃食,卻面臨著如許兇險的機關陷阱,但是,生存的艱辛,它們又能如何呢?
也是這樣的風雪天里,冷風亂竄著,雪飛舞著,一片茫茫。遭貶后的劉長卿,夜宿芙蓉山一貧苦人家,入夜時,忽聞犬吠聲聲亂,發現在屋外的雪里風里,芙蓉山主人正深一腳淺一腳地疲倦歸來——怎么不疲憊呢?這“天寒白屋貧”的人家,為生活奔忙著,在如許的風雪天里才回來!當然,詩人表面在寫芙蓉山主人,想一想劉長卿一生的命運,又何嘗不是寫的他自己?至德三年,劉長卿就被同僚使壞,因錢糧之事下獄,九死一生后,被貶到了潘州南巴。大約在公元773年至公元777年間的一個秋天,一個清涼的秋天里,由于鄂岳觀察使吳仲孺想貪污上繳的一批錢糧,但是劉長卿不想同流合污,反被陷害是“犯贓二十萬貫”。后因監察御史苗伾明察秋毫,從中斡旋,才幸免死罪,但終究還是被貶謫為睦州司馬。在屢次的不幸遭遇中,那同僚的陷害,那朝政中的污濁之氣,對于耿直的劉長卿來說,無異于一場場的風雪,但面對風雪,劉長卿又能怎樣呢?
70多年前,也是這樣的風雪天里,在抗美援朝的長津湖戰役時,沒有強大重武器和制空權的我中國人民志愿軍九兵團,為了進攻美軍的陸戰一師和第七師,實現收復新興里、咸興港等地的目標,遇上了朝鮮半島五十年一遇的極寒天氣——零下三四十攝氏度,而志愿軍們穿著的是中國南方的薄棉衣,要想進攻武器裝備精良、衣食無憂的美軍,只能夠晝伏夜出,冒著風雪苦戰。特別是九兵團的三個連隊——20軍59師177團2營6連、20軍60師180團1營2連和27軍80師242團2營5連,為了阻擊敵人后撤,臥在風雪中,不退!不逃!不動!不喊!任寒風吹,任冷雪欺,等著美軍到來……然而,美軍后撤到來時,這些連隊全部成建制地凍死在陣地上了,但埋伏姿勢沒有變,握鋼槍的姿勢沒有變,這些風雪中的英雄們,用血和生命寫下了悲壯之歌!
冬天里,風雪飛舞是一種風景,當人們賞它美麗的一面時,往往淡漠了風雪背后的一些不屈、艱辛,以及悲壯的風景,其實他們是風雪背后的另一風景,是關乎生命的狀態與精神的大風景,這風景,蒼蒼茫茫的,一眼望不到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