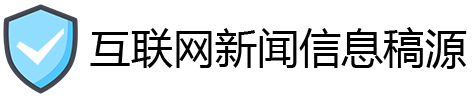盼歸 石健 攝
尹振亮
“斗笠女”,小名滿繡,八旬有三,獨自一人住在村東門的一間木樓上。木樓雖沒有雕龍刻鳳,飛禽走獸等典雅裝飾,但屋頂青瓦上的苔蘚卻在向天空昭示著什么。木樓的門梁、門廊上掛著幾頂泛黃的、大小不一的斗笠,還有幾串金黃的玉米棒。“斗笠女”滿繡阿婆,時而倚門抬手眺望,時而坐在一把竹椅上,勾著頭,對著太陽沉睡。身邊伏地的小黃狗,就是她終日的伙伴。
滿繡阿婆,不到十八歲就嫁到了我村,年輕時,她屬讓周邊十里村莊的后生仔追斷腿的靚妹子,當時嫁到劍尊大爺家,或許是因為劍尊大爺家田土多、有房住的緣故。
新婚后,滿繡阿婆和劍尊大爺成了村里村外的“形象大使”。可時隔五年過后,在一個電閃雷鳴的日子,劍尊大爺被一群穿軍裝,帶駁荷槍的人捆綁著抓走了。離開木樓時,大爺呼喚著滿繡阿婆的名字說:“滿繡啊,你把兒子帶好,我不要多久就會回來的……”聲音悠長,久久回蕩在木樓的上空。
劍尊大爺走后,沒了音信,滿繡阿婆整天數星星,望月亮,等啊、盼啊,盼呀、等呀,心里只裝著丈夫劍尊那句“你把兒子帶好,我不要多久就會回來的”話語。
滿繡阿婆出生在篾匠世家,從小就跟著爸媽學會了一門破篾的巧手藝。聽說有一年公社舉辦民間工藝比賽,她憑借手上功夫,力拔群雄,一舉奪冠,在周邊出盡了風頭。
滿繡阿婆的手上絕活不少,最牛的數她破篾織斗笠的功夫。一根竹子握在她的手上,就像一根白蘿卜,只要她的篾刀一推過去,竹片就會像鐵刨鏟刨蘿卜絲那樣,一根根“嗤嗤嗤”地拱出來。一片一公分左右厚的竹塊,經過她的手一刎,就可以削出三層厚度相宜、寬窄相等的篾片來。村民茶余飯后,都喜歡來她家門口看她刨竹篾,大家覺得是在欣賞一種藝術表演。織斗笠就像納鞋底,功夫在手上。一百六十八根篾片必須像蜘蛛織網那樣,一空不能少,每格要勻稱,走向要清晰。別人一天織不了兩頂斗笠,滿繡阿婆卻能織三頂四頂,且質量上乘,任人挑剔。
編織斗笠,用材很有講究。竹子表面一層叫頭皮篾、中間一層叫二層篾、最里面一層叫底層篾,頭皮篾織出的斗笠透亮、清澤,有柔勁,最耐用。底層篾織出的斗笠,浸水后容易發霉變黑,既不好看也不硬扎,容易腐蝕。滿繡阿婆自劍尊大爺失聯后,一直就靠著織斗笠賺錢養孩子過日子。她編織的斗笠篾片每條的長短、寬窄基本一致,斗笠邊緣工藝捆綁扎實。每次到墟上去售賣,都不用撕開喉嚨吹噓喊客,只要放在地攤上,她往邊上一站,就似坨磁鐵把客人吸引過來。
滿繡阿婆賣斗笠,還可根據個人的使用習慣和身材大小進行設計與預定,且凡是預定的斗笠,她都采用頭皮篾來編織,中間使用的斗笠葉,也是選用較寬長,無斑印,無漏孔的。阿婆斗大的字,不識幾個,但她為了防止有人欺騙她,她在預定的斗笠上,都會用小篾片編織一個只有她自己懂意思的符號鑲在斗笠頂的內垣上,免得別個懵她。按照滿繡阿婆的說法:“預定斗笠,就是預定信用,質量必須得保證。”
村后的草木一茬接一茬地輪回生長,“斗笠女”滿繡阿婆變成了“斗笠娘”。盡管她的眼淚水灌滿了村口的花溪河,而她等待的劍尊大爺卻始終沒能出現在她眼前。一些好心的親戚朋友見她日子過得清苦、孤單,跑去幫她“牽線搭橋”。她順意時,會笑著給你篩杯茶,嘮嗑幾句,告訴你,她一定要等著劍尊大爺回來。不順意時,她就會黑臉起烏云,拿根竹竿把你趕出木門坎。改革開放后,田土責任承包到戶,滿繡阿婆家缺勞力,隔壁村一位勤勞憨實的中年漢子想跟她結為夫妻,經常跑去她家幫忙耕地、蒔田、除草、收割,挑煤,賣斗笠等,平常出出進進,酷似一家人,可她就是不接受別人的殷勤,嘴里常念叨著劍尊大爺那句話:“你把兒子帶好,我不要多久就會回來的”。在她心中,有一個信念,等著、等著他回來……
到了雨天或夜晚,阿婆覺得日子難捱,她便呼喚左鄰右舍的阿哥阿婆來家閑扯閑聊,或哼唱《下洛陽》《秦香蓮》《滿姑舂碓》之類的湘昆小調;或清唱老家《十八女嫁三歲男》《罵媒婆》《娘喊女回》之類的伴嫁歌曲。每次喉嚨一打開,滿繡阿婆全身就來了神氣,麻利地找出斗笠、鍋盆、煙斗等器品當道具,到鼎鍋下去摳一把黑鍋煤,打花臉,逗得大伙捧著肚皮大笑。村里的歌頭多,大家都肯放開喉嚨,一曲接一曲地唱個沒完。滿繡阿婆人長得靚,歌也唱得好,只是唱到動情處,她有時會呼天搶地,眼淚“吧嗒吧嗒”地摔落下來,令大伙都跟著她落淚,心疚。
滿繡阿婆人勤快,又好客,每次去她家娛樂,都會備些壇子菜、花生米、紅薯干、葵花籽等“零食”,好像不花錢似的,一大碗一大盤地端出來,嘴里還一個勁地催喊著大伙多吃點,不要客氣。
見她婦道人家一個,有些心懷不軌的漢子,想到滿繡阿婆身上打“主意”,揩“油水”。聽村里人說,她每次都是拽著把篾刀,把那些“歪心”男人趕得滿街跑。久而久之,那些有想法的男人都斷了念頭,不敢再涉足滿繡阿婆的木門坎。劍尊大爺到底去了哪里呢?有人說他在臺灣那邊做了大官,早就成家立業了;有人說他在一次戰役中去堵了槍眼;也有人說他……這些,滿繡阿婆都不信。
歲月似刀,既催白了滿繡阿婆的烏發,也把她那張山花般燦爛的臉蛋雕刻成了樅樹枯般,但鐫刻在她心底的思念卻終身不老,猶如村后山林里的勁松,擎著天,扎住地。阿婆一手拉扯長大的兒子現在北方某部隊當了大官,兒媳婦帶著孩子幾次回來要接她去城市生活,頤養天年。“斗笠女”滿繡阿婆卻似懂非懂,口里反復念叨著那句話:“滿繡啊,你把兒子帶好,我不要多久就會回來的……不要多久,你爸就會回來的,我要等著,一定要在家等著。”
日出日落幾十年,“斗笠女”滿繡阿婆,仍舊坐在木屋門坎前,手扶著一頂斗笠,仰著頭,嘆著氣,望著小燕子一批批地從眼前掠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