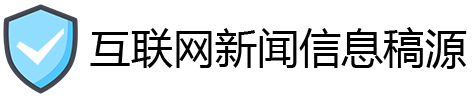金艷麗
去鳳凰,是緣于心底的一個牽盼。記得自己曾對友人說過,感覺那地方有東西在召喚我,隱隱的熱烈的長久的,在我心底似暗香一般浮動,夢幻的晨曦中它那潔白芬芳的翅膀若隱若現,展翅欲飛。于是,我便挑了某個深秋的一個好時日,尋夢去了。
從吉首火車站出來,踏上開往鳳凰的汽車,我的目光便被身旁的一對老年夫婦吸引,老太太戴著一頂黑色的毛線帽,老先生戴著一頂白色的旅游帽,他們面容和善,精神矍鑠,衣著得體。我挺喜歡老太太那對深色凹陷的眸子。那眸子一眨動,細細的靈動的光便散發出來,宛如岔開口的神秘飛袋,又好似晶晶然如鏡之新開的井水,總有新奇可貴的東西震動你內心。我總忍不住轉頭望望他們,他們饒有默契地打著手語,空氣在車廂里靜旋,旅途的美好不知不覺增添了一份。
順利到達鳳凰縣城,為摸清古城路線,我在旅游服務中心與古城外城墻間轉了好幾個回合,又在臨江一帶客棧尋覓良久,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客棧住下,天色慢慢暗下來了。客棧名為“隨緣居”,它鬧中取靜,青墻黛瓦,庭院內綠意環繞,花草蔥郁,房內布置現代簡約,風格雅致,是我歡喜的地兒。
入夜,沱江兩岸吊腳樓上的大紅燈籠漸次點亮,我走進一處吊腳樓,在某家餐飲店吃古城的特色美食,旁邊的一桌游人歡天喜地玩對山歌游戲。屋子里頓時有了明媚春日的光景,窗外亦是燈火通明。夜幕垂下來后,鳳凰的美開始絢麗奪目起來。不遠處,通體發光的萬名塔和輪廓畢現的風雨樓照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呈現出彎曲迷離的光影。所有的光似乎都射到沱江上,沱江靜靜流淌,頭尾尖翹的烏篷船在五光十色的燈影里蕩漾,各種光與影在江水上交織著,營造出一個如夢似幻的世界,令人如癡如醉。
從餐飲店走出來,我看到沱江兩岸隨處可見一盞盞扎好的河燈,紅紅的蓮花燈、玫紅色的小船燈、粉色的小豬燈,一個個惟妙惟肖,形神兼備,我忍不住買了幾盞。走到岸邊的石階上,我小心翼翼地點燃河燈,一手護著微弱的火苗,慢慢蹲下身去,將那一盞盞小小河燈交予沱江。望著這些放出去的河燈,我想起已逝的親人,思念與感動充盈心間。我暗自祈禱著,直到五盞河燈全在波動的水中消失后,才緩過神來。
翌日,我穿過青石小巷,來到沈從文先生舊居前,還未進屋,我便聞到舊居對面老字號酒鋪發出的清新彌久的酒香,腦海里立即浮現出沈老先生在孩提時代與伙伴們嬉戲打鬧、放學后一起到城墻上看風景、爬到銅炮上玩耍、他拿著酒具匆匆跑進家對面酒鋪子打酒的畫面,想象完后不禁莞爾一笑,情緒受到了感染。進了屋,發現這是一座陳舊小巧的四合院。屋里清幽典雅,書香四溢。我認真拜讀沈老留下的珍貴手稿,把他用過的書桌、搖籃、小紡車等遺物統統攝下來了,想借此沾染他的一絲靈氣。又仔細端詳鏡框中的他,年輕時的沈老眼神清亮,暮年時的他戴著眼鏡,溫和儒雅,謙和地笑著。想起他用一顆誠心,一支筆,一輩子飽含深情地寫下許多神秘動人的湘西故事,故事里滿是自然的美麗和人性的純粹,閃耀著世外桃源般的光輝,讓人無不心生眷戀和向往,莫名的感動涌上心頭。有輕柔悠揚的葫蘆絲聲從小巷深處緩緩傳來,我循聲而去,那聲音卻時斷時續,隨后杳然無跡。
我緩步來到熊希齡故居,觀完其古樸簡陋的正屋,信步來到后院,對著一棵“S”形狀的大樹發了好半天呆,靜觀發黃的樹葉片片飄落下來,一層層鋪撒在寥落的庭院里,聆聽著自己如水的心聲,一時間,仿佛時光也收住了腳步,我和所處的世界都安靜下來了。
悠悠沱江水,濃濃故人情。這里的山風、江水、吊腳樓、渡船、風俗民情早已融為一體,并相互訴說著衷情,構成一幅如詩如畫的美麗畫卷。街閭橋塔是喧鬧的,也是親水的。這里的水很清涼,水里泛著伸手可觸的柔軟飄拂的水草。鳳凰的魂除了這一江碧水,還有那矗立百年的吊腳樓,它們臨水而立,依山而筑,高低錯落有致地撐出數處歇腳地,供過往人們休養生息。從吊腳樓窗口望過去,抬眼可見悠悠江水,翠翠青山,烏篷船往來如梭,嘹亮婉轉的山歌聲在耳旁此起彼伏;打開吊腳樓大門,街巷交錯綿延,商鋪林立,商旅云集,各色產品琳瑯滿目,行人絡繹不絕。這樣似曾相識的場景,讓人像是走進沈從文先生的書中,黃永玉先生的畫里。
在鳳凰,虹橋上地下樂隊的高亢哀傷的吟唱聲和青石小巷內徐徐升起的炊煙碰撞交融,現代與傳統齊飛,各成一色;在鳳凰,你隨處可見頭上頂著高高頭帕、一心一意埋頭做手工蠟染的苗家阿婆,一臉恬淡蹲在沱江邊浣衣的婦女,她們或專注地干活,或敞開臉曬太陽,跟人閑聊家常,自然作息,一切張弛有度;在鳳凰,不管是隨意漫步,還是在溫煦的秋陽里打個盹,所有的時間與呼吸都能輕盈落地,生活變得從容、妥帖,有著實打實的安穩,能讓人感受到那份久違了的慢和美,找回最真的自我。
返程路上,我不期然地再次遇到那對老年夫婦,他們一見到我,高興地打著手勢,嘴里“咿呀咿呀”地叫起來,眼里發出暖暖細細的光。我們目光交匯,恍惚間,我已深深懂得,尋夢鳳凰,我滿載而歸。那是喧囂世俗外一方山水清幽靜謐之夢,也是我們每個人心中古老而詩意的尋根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