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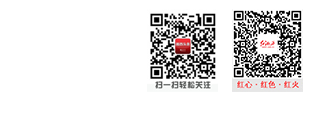
文/圖 山里人
居家隔離的時候,信手從書柜中取出《詩經》再一次閱讀。
眾所周知,《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的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先秦時期的詩歌,共311篇。其創作者佚名,絕大部分已經無法考證。其內容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風》是先秦時期各地的歌謠;《雅》是先秦時期的正聲雅樂,又分《小雅》和《大雅》;《頌》是先秦時期王庭和貴族宗廟祭祀的樂歌,又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
孔子曾概括《詩經》宗旨為“無邪”,并教育弟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頗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他們在說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說服力。至漢武帝時,《詩經》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六經》及《五經》之一。
這些詩句的內容豐富,反映了先秦時期人們的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那個時代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一面鏡子。當然,這其中,最讓我感興趣的還是“秦風”中的詩句。
因為,里耶出土了秦代簡牘,人們稱其為里耶秦簡,堪比敦煌文書、殷墟甲骨文,是為秦王朝的“百科全書”。而《詩經》“秦風”中的詩句,有許多對秦代生活場景的描寫,且又與里耶秦簡中所記錄的事物一一相對應,這其中無不閃爍著秦時的風彩迷韻。
就拿先秦時期的馬和馬車來說吧,《詩經》“秦風”中有篇題為《駟驖》的詩,這樣描寫道:“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游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這《駟驖》詩的釋義如此:四匹馬毛黑健壯,六根韁繩握手中。秦公寵愛趕車人,跟隨秦公獵一回。獵犬按時驅出大公鹿,大公鹿個個膘壯肉肥。秦公喊聲朝左射,放箭射殺則獲其鹿。狩獵結束游北園,駕輕就熟好悠閑。馬車輕快鈴鐺響,車上載著眾獵犬。
《史記·秦本記》載:秦人的先祖非子,喜好養馬,周孝王便召他在渭水一帶為周王室管理馬匹。因非子養馬有功,周孝王就分封其一個附屬國,賜給他土地,讓他接續嬴氏的祭祀,號稱秦嬴。后秦人經過數十代的努力,到秦王嬴政時,橫掃六國,一統天下。
秦人靠養馬起家,也靠騎馬打天下。這《駟驖》一詩,就是描寫秦公縱馬狩獵的場景。其實,在春秋戰國時期,狩獵就是一場場軍事演習。不難看出,秦公的這場軍事演習很是輕松愉快。
這詩句中“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就可見秦人的馬養得好,四匹馬毛黑健壯,油光亮麗。如此良馬,無不令同時代的人愛慕;再看,駕車的人手握韁繩,縱馬馳騁,好不輕松快意。
其實,在里耶秦簡中,我也讀到過良馬的相關記錄和描寫。其中一枚簡牘這樣寫道:“……酉陽傳送遷陵拔乘馬一匹,駠,牡,兩鼻,刪取左右耳前後各一所,名曰犯難……”。這是從酉陽縣(治所在今永順縣王村)送到遷陵縣(治所在今龍山縣里耶鎮)的一匹乘馬,其顏色、性別、標記和名稱等情況都作了介紹。
這簡牘中的“駠”,就是馬的顏色。《康熙字典》:“駠同駵、騮 。”《玉篇》稱:駵,赤馬黑鬣。《說文》:騮,赤馬黑毛尾也。這匹乘馬的顏色為黑鬣、黑尾巴,也算是一匹赤亮的黑馬。
還有這簡牘中的“牡”,在《駟驖》一詩也有,“奉時辰牡,辰牡孔碩。”詩中的“辰牡”是指大公鹿。《說文》:“牡,畜父也。”在甲金文字中,牡字的本義為雄性動物的泛稱,與牝相對,牝為雌性動物。因而,這匹乘馬的性別為公馬。
另外,簡牘中的“兩鼻”,應為“決兩鼻”的省略,《傳馬名籍》:“傳馬一匹,…決兩鼻”,其實就是撕裂馬的兩鼻用于套韁繩。這簡牘中的“刪取左右耳前後各一所”,應是在馬的兩耳前后各削掉一點肉,也類似我們現今在牛馬的耳上做標記,都是為了便于區別。
“輶車鸞鑣,載獫歇驕。”這是詩句中的最后一句,它描寫了狩獵回歸的場景,輕便的馬車奔馳,馬車上的鈴鐺響起,車上載著眾獵犬,當然還有所獲之獵物,一路車輪滾滾,滿載而歸。
這其中的“輶車”,就是一種輕便車,因其輕便快捷靈活,多用于春秋戰國時期的戰場上。馬瑞辰《通釋》:“輕車,古為戰車,田時葢以為副車。” 唐·楊炯《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乘使者之輶車,掌行人之旌節。” 明·唐順之《答舒云川巡按書》之二:“執事之使於江南也,輶車所至。”后世常作使者的乘車。
里耶秦簡中就有關于馬車的記錄:“敢言之:令曰上見辒輬輶乘車及。”簡牘中的“辒輬”,是古代可以臥息的馬車,也用作喪車,有窗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辒輬車。
《史記·李斯列傳》:“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辒輬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公元前210年7月,秦始皇巡游到沙丘病死。李斯認為皇帝在外面去世,又沒正式確立太子,所以就保守秘密,把秦始皇的尸體安放在一輛既能保溫又能通風涼爽的車子中,百官奏事及進獻飲食還像往常一樣。這一輛既能保溫又能通風涼爽的車子,就是辒輬車,以確保將秦始皇的尸體送回咸陽而不腐敗。因這種車載過秦始皇的尸體,后世遂為喪車。
簡牘中的“輶”,就是古代的輕便馬車。《史記·季布欒布列傳》:“朱家乃乘輶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司馬貞索隱:謂輕車,一馬車也。《晉書·輿服志》:“輶車,古之時軍車也。一馬曰輶車,二馬曰輶傳。”一般來說輶車是由車輪、車軸、車輿和傘蓋等組成。
簡牘中的“乘”,也是古代的一種輕便馬車。《說文》:“駟,馬一乘也。”就是四匹馬拉的戰車。如此看來,“辒輬”便是重型車,而“輶”和“乘”便是輕便車。有考古專家認為,這三種車都是“安車”。上古時期,乘車一般都是站立在車廂里,而安車則可以安坐,故名。達官貴族告老還鄉或徵召有重望的人,往往賜乘安車。安車多用一匹馬,禮尊者則用四匹馬。
《詩經》和里耶秦簡中關于馬和馬車的描寫紀錄還有很多,我一邊讀著《詩經》“秦風”中的詩句,一邊翻閱里耶秦簡中的記錄,無時無刻不被這習習拂面的秦風所陶醉。